|
佛家有个三字真言,佛曰“不可说”。
想想怪有意思的,似乎真是那么回事,一个人无论活得潇洒也好窝囊也罢,总会碰到那么一点两点的事儿,再大大咧咧的心思,在这样的压力下,或许就这样兜兜转转地磨出了一点“不可说”的意味来。
我不信西方的神,也不信东方的佛,并不是骨子里有能耐到可以见佛杀佛遇神杀神的气概,只是单纯的不相信。总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可能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吧。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过着顺风顺水的太平日子,偶然能有点小消遣便自娱自乐上半天。从小既没有遭遇过什么苦难,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清清白白的身世,中规中矩的生活,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成绩永远不好不坏,身边没有什么仇家,也没有什么体己的人,普普通通的一个得过且过的小和尚,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没有太多的心思去计较某个人的好坏,每天做着作为一个自然生物应该做的一切,累了便睡,醒了便如是如是,如此平淡,也如此规矩。既不找人麻烦,也不折腾自己。
想明白这些可能真的要花些时间,毕竟谁又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哪怕是魏远之这样从狗嘴里抢过罐子来的小崽子,也会在那少年心性见长的日子里,处心积虑地谋划着自己要怎样去得到一个人,狂到以为总有那么一天,或许自己就可以这样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所以说一个人的童年经历真的很重要,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魏远之八岁的时候就可以拖着个小钢管塞书包里打跑变态,与他童年里老是被人踢开被人拐卖被人用看野猫野狗的眼神看待自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所以当遇到这么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的,隔两天心情好的时候扔两个馒头心情不好的时候巴不得自己立刻消失的少年,魏远之的心里,腾现出了某种奇异的亲切感。
这个人没有对自己露出要卖掉自己的笑容,也没有用看阿猫阿狗的眼神看自己。
有多少事情是这般,开始得不明不白,认识得莫名其妙,谁也说不出是什么理由可以让这个半大的孩子起了心意,带着这个拖油瓶外加一个丑丫头跌跌撞撞地一路行来,还就这样磕磕碰碰地和这个捡来的便宜弟弟走在了一起。
人生真是妙不可言,哪怕充满了苦难,也要在一个突兀的拐弯口冒出个尖儿吓人一跳,好似这样才能多出多少乐趣。什么忧郁的少年,什么闺中的怨女,都成了这个不可撼动的命运下的一个逗趣的知了。
聒噪得要死,还不知收敛地把好容易拼好的卡片打得支离破碎。
魏远之之于魏谦的执着,或许也算是“不可说”的一种世俗的表达吧。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的处心积虑,为了另一个人的神魂颠倒,爱得太过惊世骇俗,不能被所爱的人发现的心思,也算是“不可说”的境界了吧。我呢,总归不过是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没有太多的志气,甚至没有太多的追求,骨子里都在彻头彻尾叫嚣着一种名为好逸恶劳的可耻性子,小时候有过的一些幻想一些打算,都在还没来得及彻底踏入社会之前便泯灭得几乎干干净净。人长大之后总会变得讨厌,说的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年纪还不大,心思已经步入暮年,可能就是这样吧。
魏远之那样如有野狗一样的经历我没有,那样剑拔弩张,为了得到自己所求而不顾一切的坚韧甚至于疯狂,我更没有。
这种不可言说的比较,更加坐实了我的平庸。
总不会有人在这种天差地别的对比中还能保持着愉悦的心境的。真是作得一手好死。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魏谦,也就没有了后来的魏远之了。真的有人可以为了另一个人倾尽所有吗?又真的有人可以为了另一个人神魂颠倒吗?
我不知道,也不打算这样。
魏远之越活越“薄”,古时的那种妖器也是如此,剑走偏锋,薄得最后甚至只剩下了一层刃。可人到底不是剑器,薄得过分了,物极必反,伤人害己。
所幸两人最后终于走在了一起,在同患难共生死那么多次那么多年之后,在魏远之想了那么多疼了那么深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大哥走在了一起。
美得就像一场梦,生怕睁开眼来一看,发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自己无数次幻想中的一次,注定是镜花水月,心中所想所爱的那个人,永远就像隔了块玻璃的蜡像,触不可及。一场不可说,终于变成了一场可以共同言说,只有彼此才知道的低眉细语。
人活得“薄”点,或许真的会过刚易折,或许,真的会不太太平吧。安逸的日子过久了,难免就会忍不住想要作死,折腾得久了,恍惚才会发现,自己这样的安逸,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人总要有个努力的理由,向上的理由,为了自己也好,为了别人也罢,总不能就这样混吃等死,人云亦云。
总不能真的白来一趟,瞎掰着活着,活着活着,连自己都忘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就这样忘记了或许有过或许已经消失殆尽了的梦想。不是不甘心什么的,也不是像某个小崽子那样痴迷得神魂颠倒什么的,只是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但凡这个年龄的,无论是魏远之还是我,总不应该暮气沉沉,除了玩乐之外,再无他长。好像这样才算是有了点活着的意思。
佛曰,不可说。说了,都是错。
啧啧,不说,还不是等着自己强大到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也没有人能拦敢拦的时候吗?
我这种人,简直是在败坏佛门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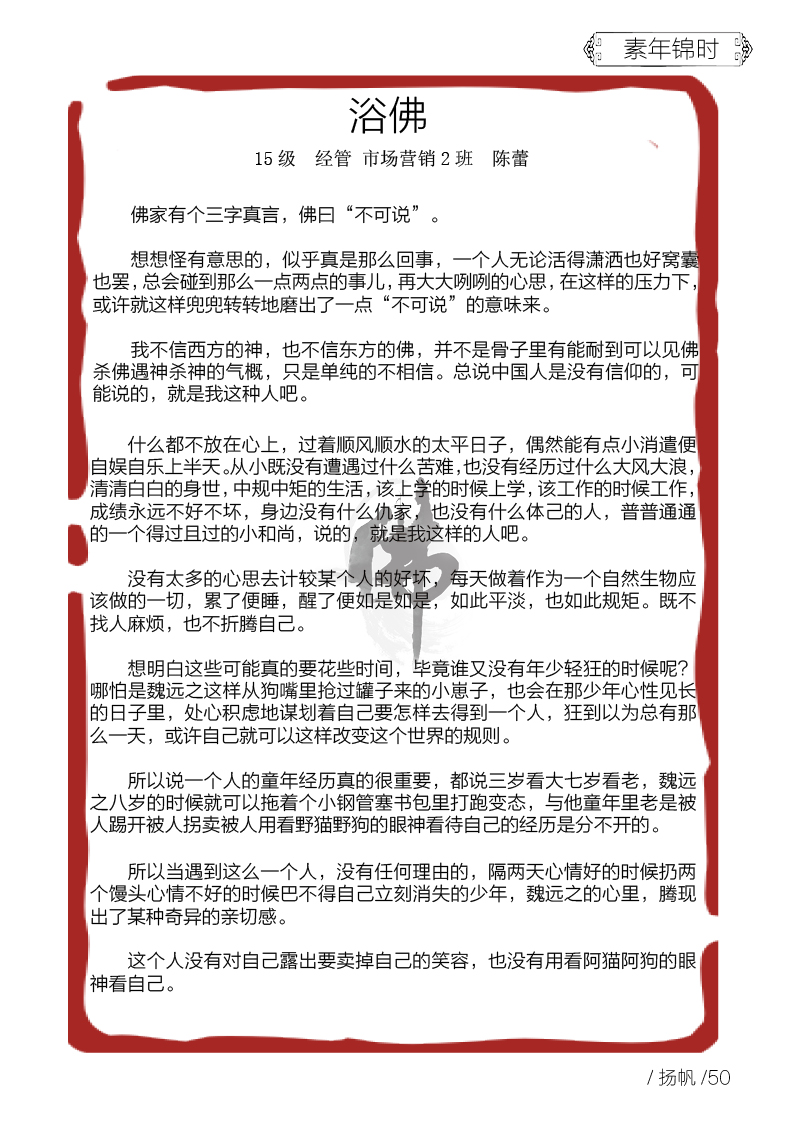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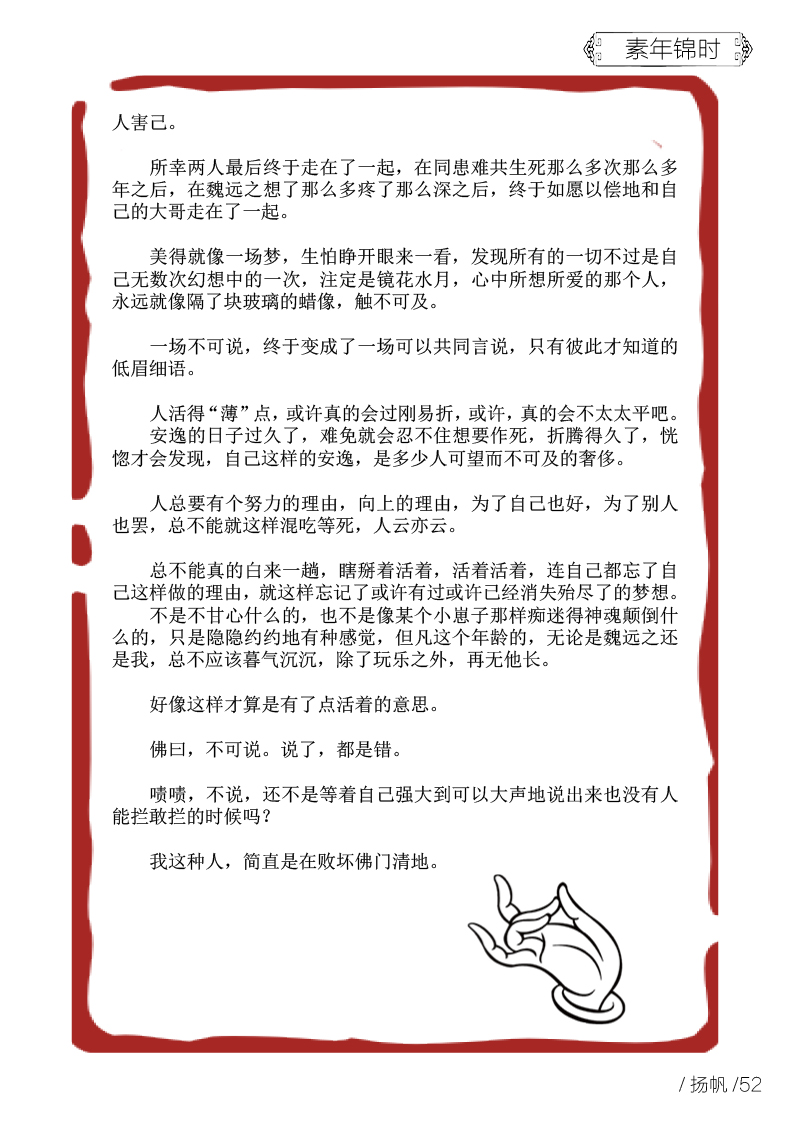
|